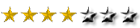長毛在2012年9月25日作出的認罪求情詞
本案發生在2011年7月1日 七一遊行,一眾被告被控組織及參與非法集會罪
最後各人被判罰款一千五百元
1979年6月5日我被判入獄一個月,年代久遠,我不認為法庭會以此犯罪記錄作判刑參考,然而我認為我有責任解釋。當日我為了聲援政治犯魏京生而去新華社示威,我被指未經警務處處長同意而集會,視為非法集會。當時新華社是中國政府駐港最高機構。我相信以裁判官 閣下的年紀,應該知悉魏京生。回歸後,新華社已經變為純粹的新聞社,為國內政治犯請命的示威,都去了中聯辦門外進行,我相信裁判官 閣下都知道此機構。
中聯辦門外允許示威。我明白,警察與示威者的角度不同,同時中聯辦對不同的示威有不同的態度,當香港人行使《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有示威、集會、罷工的自由,在不同時候有不同的處理:意思就是,某些時候警方會干預或施加條件。
裁判官 閣下可看到,時代轉變,社會更趨寬容,更注重人權。1979年我在新華社門外唱歌、叫口號,就被判監。三十多年前,援引相同的法例,在社會價值觀不同的時空,得出不同的判刑。另一著名案例,是2002年我與兩位學聯同學公民抗命,我們認為今日我被控的罪名不合憲,是壓制香港人根據《基本法》二十七條的示威自由,當時我真的未經批准而在遮打花園集會,警方當時曾警告:「梁生,你們的集會未經申請,你們有可能被拘捕」,我們的行動正正為了凸顯條例的荒謬。事實上,當裁判官 閣下翻看我的犯案紀錄第十一項,即上述2002年的案件,一群人舉辦和平集結,去警察總部門外陳述關於《公安條例》17A(3) 第245條,我們認為集會須經警務處處長批准才可舉行,這制度是不合憲的。
裁判官 閣下,邏輯學有術語叫「悖論 (paradox)」,當公民因一條過時的《公安條例》內最不合理的規定而被警方或政府剝奪權利,而因此舉行示威,同樣面對公權力的壓制。我和兩位學聯同學被檢控與今日同樣的控罪,該案我們上訴至終審法院,我們敗訴,這就是我今天認罪的原因:在法律觀點上,已經無對質的空間。我身為立法會議員,政府依賴不合憲法例壓制市民憲法權利,我當然明白這不能在法院內解決,除非連法庭都感受到社會風氣的震撼,而不得不作出裁決。
裁判官 閣下,我在2002年經歷了一年多的法律訴訟,最終終審庭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先生稱(參考 [已轉換文字為連結] 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45653&QS=%28{%24leung+kwok+hung}+%25parties%29&TP=JU&currpage=T),在公安條例下,倘若警務處處長依據 “ordre public” 的概念去執法不合適,因為廣泛的概念很容易被政府濫用,他裁決,警務處處長衡量是否批准集會時,應該將 “ordre public” 的概念剔除。
裁判官 閣下,由1979年至2002年,再來到今日,我們面對同樣的「悖論」:到底1968年暴動後所立的公安法,是否合乎時宜?到底警務處處長或其授權代表,有否權力在和平集會下貿然稱集會未申請,未申請本身就是罪。這與言論入罪無分別:你可以發言,但如果我不喜歡你的發言,或我認為你的發言對社會有害,我有權檢控你。
裁判官 閣下,我認為檢控當局提出的證據亦是如此,當日是七一遊行,自O三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每年都有十萬以上市民在街道上,藉回歸週年表達訴求;如同警方描述的案情,通常參加者都由一定機構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終點在政府總部。案發當日,因遊行人數太多,我們屬於「隊尾」,警方說辭是,由於示威限時至晚上八點,過了八點就不能再到政府總部示威。裁判官 閣下,如果你在餐廳用膳,吃了一半後侍應生告訴你「限時15分鐘」,因為你過時而不容許你吃下去,你認為這侍應荒謬嗎?在本案,警務處處長和警員是公務員,服務對象是市民,市民根據基本法二十七條行使自由,亦根據警務處處長批准行使自由,只因為太多市民上街而無法如期到達警察規定的地點,就被剝奪憲法性的權利,警察當日執法與我上述比喻中橫蠻無理的侍應有何分別?
裁判官 閣下,請你考慮,倘若當日如往年一樣被允許在政府總部外繼續表達訴求,由於政府總部是政府物業,大抵亦會如往年一樣,在政府申請下,警察協助保安將通宵留守的示威者抬走,就無須由警察援引公安條例將示威者拘捕,我相信 閣下亦經常在傳媒看到。在反對國民教育抗爭中,無論是示威者聲稱的九萬人,還是警方聲稱的四萬人,都是不請自來,即使有申請,都不是申請無限期的集會,即是說,市民為社會伸張公義,是天然的決定,政府有量度,應容許市民示威,警察無須擔當任何角色。九萬人在我辦公室樓下,添美道被封了,我都覺得很不便,其他市民都感覺到不便是正常的。問題是,其他市民感受到不便,是否必然凌駕示威自由?這是值得斟酌的。如是說,每年七一最少有三次令到市民不便,第一次就是早上由政府贊助的慶祝回歸大遊行,有數小時完全佔用港島鬧市的行車線,下午另一批人,晚上則燒煙花;任何示威都會對他人構成不便。
案發當日,政府拒絕我們前往原本讓我們示威的地點,故此我們不能不在馬路聚集,這是事件的開端。當然有人可聲稱,我們可以不在馬路聚集,改到遮打花園。這是另一個悖論:即使我們聽從警方建議去了遮打花園,根據此條例,我們一行幾百人到了遮打花園,可否因為聽從警方吩咐而免除被檢控呢?肯定不會的,因為這是未經申請的集結,不論地點在遮打花園還是馬路,任何負責公眾活動的警務人員可以隨時宣佈這是非法集會,就如同我在2002年在遮打花園集會一樣。故此,這條例的執法,不以參加者在何時何地何種目的何種態度舉行集結為依歸,而是以警務處處長的絕對權力為依歸。即使當日我們無做過案情描述的事,只要警務處處長決定追究,我們已經犯法了。
裁判官 閣下,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在美國伯明翰非法集會,被控以我相約的罪名(參看: [已轉換文字為連結]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rmingham_campaign),在他向教會的反對者的自辯書《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如是說:We know through painful experience that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 Frankly, I have yet to engage in a direct action campaign that was "well timed" in the view of those who have not suffered unduly from the disease of segregation. For years now I have heard the word "Wait!" It rings in the ear of every Negro with piercing familiarity. This "Wait" has almost always meant "Never." We must come to see, with one of our distinguished jurists, that "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教會的人質疑他帶領黑人在伯明翰示威是玷污上帝,故此他撰文反駁。黑人被剝奪選舉權三百四十年,太久了,他必須直接行動。我不是黑人,我都不接受以種族主義剝奪黑人選舉權。我是中國人,我在回歸後等了十五年,現在我是享有特權的人,我可以選舉特首。我們站在法庭,為了一個簡單目的,不是甚麼崇高的目的,只是人最本能的目的:我要公平。
裁判官 閣下,我們被指擾亂公眾秩序,或者我們被指魯莽,不向警務處處長申請集會。「本能」不能預先知道,「本能」不能申請,我希望 閣下明白,香港不合理的制度,孕育更多不合理的事物,我不在此列舉了。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就是運用表達的權利,去令馬丁路德金所講「被延遲的公義(justice delayed )」有機會被看到,有機會提早實現。當晚我們就是做這些事情。
裁判官 閣下,在控方案情中的那群人,由本身可以在政府管有的地方示威,被驅趕到馬路上,我們的尊嚴已經被踐踏。即使我們聲音微弱,我們都要重拾尊嚴,在馬路上示威,我們希望有人知道,在幾十萬人示威後,問題仍然未解決。閣下在聆聽案情時已經知悉,我們要求曾蔭權或其代理人聆聽我們的訴求;我對梁振英無好感,但他的確表現不同,他見到了四至九萬人集會稱「不要洗腦教育」時,他親自出來見示威人士。為何在年多後的梁特首可以這樣做,年多前的曾特首做不到?莫非又有鮑魚晚宴?
我們的所作所為,不會令 閣下、控方乃至整個社會感到愉快,因為我們令很多人覺得麻煩。但為何我們還要做?就是因為公義來得太遲。本案被告來自不同組織群體,是誰讓五湖四海的人不約而同到馬路集會?我們務須感謝曾蔭權先生,就是因為他的傲慢,他不讓人在他的政府前示威,令本來想去政府總部示威的人在馬路集會。我們怎會預先知道特首如此傲慢?我們怎能預先申請「倘若曾蔭權傲慢的時候,我們改為到遮打花園示威」?現有《公安條例》下,警務處處長對集會可以有非常細緻的規範, 閣下可參考遊行集會的申請表,然後警務處根據我們的申報而施加條件。我們怎可預料未來?
我想起一則成語《刻舟求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我們的社會如斯複雜,我們的政治制度如斯不合理,由是產生的自發或有組織示威,千差萬別五花八門,怎能預先知道?在《公安條例》下,超過30人的遊行或50人的集會,就須要事先申請。政治制度上的腐敗不堪,不應該由 閣下處理,《公安條例》殘舊,以處理暴動為基礎而訂立的暫時性法例,殘存至四十多年後。
我有很大感觸。四年前我去孫明揚局長住家樓下示威,告訴他不可將公屋租金封頂機制切銷,否則公屋居民必定受害。自那時起,公屋居民的租金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我因此被裁定非法集會而付出六十小時社會服務令。我未能成功阻止公屋加租,卻換來懲罰,我失敗了。四年前我被指要突破警方防線,這次我們卻前來被拘捕;我們身先士卒反對不義制度,不值得羞愧,不值得反抗,不值得與警察糾纏,亦不值得在法庭糾纏。我所以如此長篇大論,是因為根據法庭規定,同案被告委托了律師答辯而不能自辯,而我則在徵得他們同意前就代他們說話,一切錯的,請放在我身上,如有道理的,請你加諸他們。
裁判官 閣下,我們認罪,因為我們知道鐵案如山,不想為案情浪費大家的青春,縱使在心中我們認為自己無罪。我們的求情,不是求刑事罪案的輕判,我們的求情,是希望法治精神之下的公平得到彰顯。
我在此向 閣下請求,給予本案被告最輕的懲罰,因為他們只是爭取原本應有的權利,受壓迫只因過時的法例。卡斯特羅接受軍事法庭審訊的時候如是說:「判我有罪吧!無所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法庭審理的是人間的罪(Crime),是一批人代表社會去定罪,隨時間地點可變;我今日所講的是Sin,是每人內心對自己責任的期許而引發的罪惡感。我們是有罪的,而政府所犯的罪不會在此審理,因為她的罪是原罪。
感謝 閣下撥冗容許我發言,我重申希望 閣下處以最輕的刑罰。
本案發生在2011年7月1日 七一遊行,一眾被告被控組織及參與非法集會罪
最後各人被判罰款一千五百元
1979年6月5日我被判入獄一個月,年代久遠,我不認為法庭會以此犯罪記錄作判刑參考,然而我認為我有責任解釋。當日我為了聲援政治犯魏京生而去新華社示威,我被指未經警務處處長同意而集會,視為非法集會。當時新華社是中國政府駐港最高機構。我相信以裁判官 閣下的年紀,應該知悉魏京生。回歸後,新華社已經變為純粹的新聞社,為國內政治犯請命的示威,都去了中聯辦門外進行,我相信裁判官 閣下都知道此機構。
中聯辦門外允許示威。我明白,警察與示威者的角度不同,同時中聯辦對不同的示威有不同的態度,當香港人行使《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有示威、集會、罷工的自由,在不同時候有不同的處理:意思就是,某些時候警方會干預或施加條件。
裁判官 閣下可看到,時代轉變,社會更趨寬容,更注重人權。1979年我在新華社門外唱歌、叫口號,就被判監。三十多年前,援引相同的法例,在社會價值觀不同的時空,得出不同的判刑。另一著名案例,是2002年我與兩位學聯同學公民抗命,我們認為今日我被控的罪名不合憲,是壓制香港人根據《基本法》二十七條的示威自由,當時我真的未經批准而在遮打花園集會,警方當時曾警告:「梁生,你們的集會未經申請,你們有可能被拘捕」,我們的行動正正為了凸顯條例的荒謬。事實上,當裁判官 閣下翻看我的犯案紀錄第十一項,即上述2002年的案件,一群人舉辦和平集結,去警察總部門外陳述關於《公安條例》17A(3) 第245條,我們認為集會須經警務處處長批准才可舉行,這制度是不合憲的。
裁判官 閣下,邏輯學有術語叫「悖論 (paradox)」,當公民因一條過時的《公安條例》內最不合理的規定而被警方或政府剝奪權利,而因此舉行示威,同樣面對公權力的壓制。我和兩位學聯同學被檢控與今日同樣的控罪,該案我們上訴至終審法院,我們敗訴,這就是我今天認罪的原因:在法律觀點上,已經無對質的空間。我身為立法會議員,政府依賴不合憲法例壓制市民憲法權利,我當然明白這不能在法院內解決,除非連法庭都感受到社會風氣的震撼,而不得不作出裁決。
裁判官 閣下,我在2002年經歷了一年多的法律訴訟,最終終審庭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先生稱(參考 [已轉換文字為連結] 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45653&QS=%28{%24leung+kwok+hung}+%25parties%29&TP=JU&currpage=T),在公安條例下,倘若警務處處長依據 “ordre public” 的概念去執法不合適,因為廣泛的概念很容易被政府濫用,他裁決,警務處處長衡量是否批准集會時,應該將 “ordre public” 的概念剔除。
裁判官 閣下,由1979年至2002年,再來到今日,我們面對同樣的「悖論」:到底1968年暴動後所立的公安法,是否合乎時宜?到底警務處處長或其授權代表,有否權力在和平集會下貿然稱集會未申請,未申請本身就是罪。這與言論入罪無分別:你可以發言,但如果我不喜歡你的發言,或我認為你的發言對社會有害,我有權檢控你。
裁判官 閣下,我認為檢控當局提出的證據亦是如此,當日是七一遊行,自O三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每年都有十萬以上市民在街道上,藉回歸週年表達訴求;如同警方描述的案情,通常參加者都由一定機構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終點在政府總部。案發當日,因遊行人數太多,我們屬於「隊尾」,警方說辭是,由於示威限時至晚上八點,過了八點就不能再到政府總部示威。裁判官 閣下,如果你在餐廳用膳,吃了一半後侍應生告訴你「限時15分鐘」,因為你過時而不容許你吃下去,你認為這侍應荒謬嗎?在本案,警務處處長和警員是公務員,服務對象是市民,市民根據基本法二十七條行使自由,亦根據警務處處長批准行使自由,只因為太多市民上街而無法如期到達警察規定的地點,就被剝奪憲法性的權利,警察當日執法與我上述比喻中橫蠻無理的侍應有何分別?
裁判官 閣下,請你考慮,倘若當日如往年一樣被允許在政府總部外繼續表達訴求,由於政府總部是政府物業,大抵亦會如往年一樣,在政府申請下,警察協助保安將通宵留守的示威者抬走,就無須由警察援引公安條例將示威者拘捕,我相信 閣下亦經常在傳媒看到。在反對國民教育抗爭中,無論是示威者聲稱的九萬人,還是警方聲稱的四萬人,都是不請自來,即使有申請,都不是申請無限期的集會,即是說,市民為社會伸張公義,是天然的決定,政府有量度,應容許市民示威,警察無須擔當任何角色。九萬人在我辦公室樓下,添美道被封了,我都覺得很不便,其他市民都感覺到不便是正常的。問題是,其他市民感受到不便,是否必然凌駕示威自由?這是值得斟酌的。如是說,每年七一最少有三次令到市民不便,第一次就是早上由政府贊助的慶祝回歸大遊行,有數小時完全佔用港島鬧市的行車線,下午另一批人,晚上則燒煙花;任何示威都會對他人構成不便。
案發當日,政府拒絕我們前往原本讓我們示威的地點,故此我們不能不在馬路聚集,這是事件的開端。當然有人可聲稱,我們可以不在馬路聚集,改到遮打花園。這是另一個悖論:即使我們聽從警方建議去了遮打花園,根據此條例,我們一行幾百人到了遮打花園,可否因為聽從警方吩咐而免除被檢控呢?肯定不會的,因為這是未經申請的集結,不論地點在遮打花園還是馬路,任何負責公眾活動的警務人員可以隨時宣佈這是非法集會,就如同我在2002年在遮打花園集會一樣。故此,這條例的執法,不以參加者在何時何地何種目的何種態度舉行集結為依歸,而是以警務處處長的絕對權力為依歸。即使當日我們無做過案情描述的事,只要警務處處長決定追究,我們已經犯法了。
裁判官 閣下,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在美國伯明翰非法集會,被控以我相約的罪名(參看: [已轉換文字為連結]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rmingham_campaign),在他向教會的反對者的自辯書《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如是說:We know through painful experience that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 Frankly, I have yet to engage in a direct action campaign that was "well timed" in the view of those who have not suffered unduly from the disease of segregation. For years now I have heard the word "Wait!" It rings in the ear of every Negro with piercing familiarity. This "Wait" has almost always meant "Never." We must come to see, with one of our distinguished jurists, that "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教會的人質疑他帶領黑人在伯明翰示威是玷污上帝,故此他撰文反駁。黑人被剝奪選舉權三百四十年,太久了,他必須直接行動。我不是黑人,我都不接受以種族主義剝奪黑人選舉權。我是中國人,我在回歸後等了十五年,現在我是享有特權的人,我可以選舉特首。我們站在法庭,為了一個簡單目的,不是甚麼崇高的目的,只是人最本能的目的:我要公平。
裁判官 閣下,我們被指擾亂公眾秩序,或者我們被指魯莽,不向警務處處長申請集會。「本能」不能預先知道,「本能」不能申請,我希望 閣下明白,香港不合理的制度,孕育更多不合理的事物,我不在此列舉了。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就是運用表達的權利,去令馬丁路德金所講「被延遲的公義(justice delayed )」有機會被看到,有機會提早實現。當晚我們就是做這些事情。
裁判官 閣下,在控方案情中的那群人,由本身可以在政府管有的地方示威,被驅趕到馬路上,我們的尊嚴已經被踐踏。即使我們聲音微弱,我們都要重拾尊嚴,在馬路上示威,我們希望有人知道,在幾十萬人示威後,問題仍然未解決。閣下在聆聽案情時已經知悉,我們要求曾蔭權或其代理人聆聽我們的訴求;我對梁振英無好感,但他的確表現不同,他見到了四至九萬人集會稱「不要洗腦教育」時,他親自出來見示威人士。為何在年多後的梁特首可以這樣做,年多前的曾特首做不到?莫非又有鮑魚晚宴?
我們的所作所為,不會令 閣下、控方乃至整個社會感到愉快,因為我們令很多人覺得麻煩。但為何我們還要做?就是因為公義來得太遲。本案被告來自不同組織群體,是誰讓五湖四海的人不約而同到馬路集會?我們務須感謝曾蔭權先生,就是因為他的傲慢,他不讓人在他的政府前示威,令本來想去政府總部示威的人在馬路集會。我們怎會預先知道特首如此傲慢?我們怎能預先申請「倘若曾蔭權傲慢的時候,我們改為到遮打花園示威」?現有《公安條例》下,警務處處長對集會可以有非常細緻的規範, 閣下可參考遊行集會的申請表,然後警務處根據我們的申報而施加條件。我們怎可預料未來?
我想起一則成語《刻舟求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我們的社會如斯複雜,我們的政治制度如斯不合理,由是產生的自發或有組織示威,千差萬別五花八門,怎能預先知道?在《公安條例》下,超過30人的遊行或50人的集會,就須要事先申請。政治制度上的腐敗不堪,不應該由 閣下處理,《公安條例》殘舊,以處理暴動為基礎而訂立的暫時性法例,殘存至四十多年後。
我有很大感觸。四年前我去孫明揚局長住家樓下示威,告訴他不可將公屋租金封頂機制切銷,否則公屋居民必定受害。自那時起,公屋居民的租金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我因此被裁定非法集會而付出六十小時社會服務令。我未能成功阻止公屋加租,卻換來懲罰,我失敗了。四年前我被指要突破警方防線,這次我們卻前來被拘捕;我們身先士卒反對不義制度,不值得羞愧,不值得反抗,不值得與警察糾纏,亦不值得在法庭糾纏。我所以如此長篇大論,是因為根據法庭規定,同案被告委托了律師答辯而不能自辯,而我則在徵得他們同意前就代他們說話,一切錯的,請放在我身上,如有道理的,請你加諸他們。
裁判官 閣下,我們認罪,因為我們知道鐵案如山,不想為案情浪費大家的青春,縱使在心中我們認為自己無罪。我們的求情,不是求刑事罪案的輕判,我們的求情,是希望法治精神之下的公平得到彰顯。
我在此向 閣下請求,給予本案被告最輕的懲罰,因為他們只是爭取原本應有的權利,受壓迫只因過時的法例。卡斯特羅接受軍事法庭審訊的時候如是說:「判我有罪吧!無所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法庭審理的是人間的罪(Crime),是一批人代表社會去定罪,隨時間地點可變;我今日所講的是Sin,是每人內心對自己責任的期許而引發的罪惡感。我們是有罪的,而政府所犯的罪不會在此審理,因為她的罪是原罪。
感謝 閣下撥冗容許我發言,我重申希望 閣下處以最輕的刑罰。